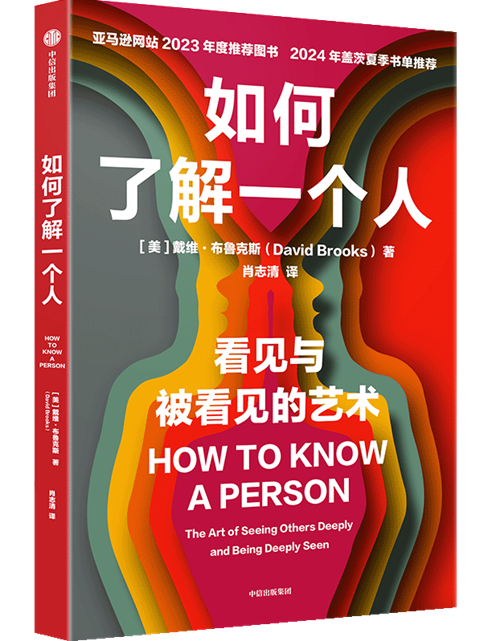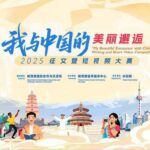芭芭拉·拉齐尔·阿舍尔的丈夫鲍勃在获知检测结果后,以尽可能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告知了她结果:“好像是胰腺癌。”医生说他只能活3个月。
在芭芭拉和朋友们的张罗下,丈夫临终的日子过得格外精彩。他们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派对,其中一场是俄罗斯主题之夜,大家品尝鱼子酱和伏特加;另一场则是夏威夷主题之夜,所有人身着草裙,头戴散发着茉莉花香的花环。此外,他们还一起品读诗歌,畅谈心事。芭芭拉在她的回忆录《失联》(Ghosting)中这样写道:“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能够激励我们成为更好、更坦诚、更勇敢的自己。”她补充说:“有很多次,我们都感到很幸运,就好像死亡赋予了我们额外的生命。”
在鲍勃的病情日益恶化之后,芭芭拉果断地把他从医院接回家,让他能在家中得到更细致、更人道的照料。芭芭拉为丈夫倾注了无尽的爱与关怀。“死亡是一种亲密的体验,这一次我贴得很近,”芭芭拉写道,“在这漫长的离别中,我们心灵相通,紧密相连。”
接受丈夫的死亡固然艰难,可就在他离世之后,悲痛更为沉重。追悼会和守灵结束后,芭芭拉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周围弥漫着一种沉寂。她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仿佛有一阵风从我空洞的躯壳中吹过。”一天,她在过马路时迎面碰到5年前痛失丈夫的邻居,邻居突然叫住了她:“你或许以为自己能保持理智,但实际上你做不到。”不久之后,她就在CVS药店的同事面前突然情绪爆发,因为音响里播放着《我会回家过圣诞节》,而丈夫却再也无法与她一起过圣诞节了。她开始害怕独自洗澡、听歌和过周末。她开始把自己的东西送人,送完之后又感到后悔不已。她时常幻想在街头与丈夫再次相遇的情景。
C.S.刘易斯曾指出,悲伤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一条穿越漫长山谷的河流,在每一个转弯处,都会呈现出新的风景。然而,这条河流总是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轨迹。悲伤和痛苦往往会打破我们对自己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基本假设。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个世界是仁慈的,人生是可控的,事物本应富有意义,我们都是好人,都会有好报。而苦难和失去却将这一切粉碎。
“创伤挑战了我们的整体意义系统,”史蒂芬·约瑟夫在《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一书中写道,“它让我们直面人生的诸多真相,而这些真相却与我们的意义体系相冲突。我们越是努力地固守自己的臆想世界,就越会深陷于对这些真相的否认。”
那些经历了永久性创伤的人,会努力将所承受的痛苦融入现有的模式。而那些持续成长的人,则会努力适应所发生的一切,进而塑造出全新的模式。前者会说:“我战胜了脑癌,未来我会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而后者会说:“不,癌症改变了我。虽然我挺过了癌症。但它让我重新思考我要如何度过每一天。”重塑我们的模式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基本问题:世界在哪些方面是安全的,哪些方面是危险的?有没有一些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我是谁?我在世界上的定位是什么?我的故事是怎样的?我真正想要去哪里?何种神明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重塑模式的过程颇为艰辛,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在调查那些经历过火车爆炸和其他恐怖袭击的人们后,约瑟夫发现,46%的人表示他们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悲观,而43%的人则表示他们的生活态度变得更加乐观。重新审视和重塑自我的旅程通常需要我们开启斯蒂芬·科普所说的“夜海之旅”。这个概念源自卡尔·荣格,它意味着我们要勇敢地航行在内心深处的海洋,去探索“被分裂、被否认、不为人知、不受欢迎、被抛弃”的自我世界。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必须知道他在遭受不幸之前是什么样的人,经历不幸后又如何重塑整个人生观。如果说本书的潜台词是“经历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事情”。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经验就是,要了解一个悲伤的人,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如何面对不幸。他们是否因此变得更加睿智、更加善良、更加坚强?又或者因此一蹶不振、迷茫无助、恐惧不安?要想成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善良之人,你必须知道如何陪伴一个人走过这个过程。
1936年秋天,黎明时分,年仅10岁的弗雷德里克·布赫纳早早地醒来。他和8岁的弟弟兴奋不已,因为父母要带他们去看一场足球比赛。他们激动的原因并非比赛本身,而是因为全家人,包括祖母,将一同出游,享受美食、欢乐和冒险的时光。当时时间尚早,两个男孩还躺在床上。突然间,房门轻轻打开,父亲的目光透过门缝投向他们。多年后,兄弟俩都不记得父亲当时是否对他们说了些什么。那好像只是任何一个家长为确保家人安全都会做的随意检查。
不久后,他们听到了一声尖叫,随后是开门、关门的声音。 他们从窗户望出去,只见父亲躺在砾石车道上,母亲和祖母光着脚,身上还穿着睡衣,俯身在他身旁。两人一人抓住父亲的一条腿,像操作水泵手柄一样,一起抬高和放下。附近的车库大门敞开着,蓝色的烟雾从里面滚滚涌出。
一辆救护车在车道口猛然停下,医生急忙从车内钻出,蹲在父亲身旁检查。检查完后,医生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已经无能为力。他们的父亲死于毒气自杀。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找到父亲的遗书,遗书用铅笔写在《飘》的最后一页,是写给母亲的一段话:“我倾慕你,深爱着你,但我却一无是处……请把我的手表给弗雷迪,珍珠别针给杰米。而你,请接受我全部的爱。”
一两个月后,母亲决定带着全家人前往百慕大生活。然而,祖母并不同意他们去,坚持让他们“留下来面对现实”。几十年后,布赫纳对于祖母的决定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写道:“面对现实的冷酷无情,我们不能选择逃避。如果我们闭上眼睛不去正视它,黑暗的力量将会从背后乘虚而入,在我们毫无防备之时发起突然袭击。”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喜欢百慕大,那里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治愈。
他后来写道:“我们都会在人生的旅途中塑造自己的现实。对我而言,现实意味着在走出父亲离世的阴影后,我迎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更加幸福……不能说我已不再悲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没有像我弟弟那样真正感受到那种悲伤。但我的悲伤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推迟了30年。”
那是一段心灵封闭的岁月。父亲自杀一年后的某天,布赫纳看到弟弟在哭泣,便问他怎么了。当他意识到弟弟是在为父亲而哭泣时,他十分震惊。他以为自己早已摆脱了那种痛苦。母亲也关闭了自己的情感大门。父亲自杀后,布赫纳再也没有看到母亲哭泣过,之后他们也很少谈起父亲。母亲原本是个热情的人,有时也很慷慨,但她对别人和自己的苦难都保持沉默。布赫纳回忆道:“别人的悲伤,即使是她所爱的人的悲伤,似乎从未触及她的内心深处。”
几十年后,布赫纳深刻地领悟到:“用坚如钢铁的心灵来抵御现实世界的残酷所带来的麻烦是,这种钢铁般的保护也可能使我们的内心变得封闭,无法接受源自生命本身的神圣力量的改变。”
布赫纳不可能永远封闭自己的内心。他成了一名教师和小说家。很多年前,布赫纳曾前往母亲位于纽约的公寓探望她。有一天,他们正要坐下来吃晚饭,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打给他的。电话那头,一个朋友声音颤抖、泣不成声,他在机场刚刚得知父母和怀孕的姐姐在一场车祸中遭遇不幸,生死未卜。朋友问布赫纳能否在飞机起飞前到机场陪他。布赫纳告诉母亲他必须立刻动身去机场。母亲听后觉得整件事情很荒唐。她不明白,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要求别人去机场陪自己?这样做究竟有何意义?为何要毁掉他们俩都期待已久的晚上呢?
他母亲所表达的想法,正是他刚刚在脑海中闪过的。但当他听到母亲说这些话时,他的内心却涌起了一股厌恶。母亲怎么会如此冷酷无情,对他朋友的痛苦无动于衷?几分钟后,朋友打来电话,说另一个朋友刚刚答应来机场陪他,因此他不用再过来了。这段经历对布赫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他开启了一段新的旅程。父亲自杀之日起停止的时间仿佛又重启了。
接下来,布赫纳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究之旅,探究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突然对隐藏在表面和背后的事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我的外表之下,我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开始探索这一主题,尽管方法还不太成熟。”他意识到,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在他看来,在这段旅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自己的痛苦,并通过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人面对他们的痛苦。
于是,布赫纳决定追寻父亲的足迹。他想了解父亲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结果发现,他的家庭里有2个人自杀,3个人终日酗酒。每当布赫纳遇到认识他父亲的人,他总要问他们自己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们的回答并不能让他满意。在他们口中,他的父亲是富有魅力、英俊潇洒的优秀运动员。谁也无法解答这个深层的谜团:在父亲内心深处潜伏的恶魔究竟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走向那个悲剧的结局?
到了中年,布赫纳一想起父亲就会落泪。他在晚年写道,他没有一天不思念父亲。他已经蜕变成一位满怀同情心、有坚定信仰和人性光辉的作家。他逐渐认识到,挖掘他人的生命故事并不是一项孤独的活动。正是通过与他人分享悲伤,一起思考悲伤的意义,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克服恐惧,在最深层次上了解彼此。在《说个秘密》(Telling Secrets)一书中,布赫纳写道:“或许我们最渴望的是以我们的完整人性示人,然而这往往也是我们最害怕的。时不时地展示我们真实、完整的一面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失去真实、完整的自我,渐渐地接受那个经过高度修饰的自我,我们也希望修饰后的自己更被世人所接纳。说出我们的秘密同样重要,因为这样会让其他人更愿意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两个秘密。”
布赫纳模式是人们熟知的一种模式。当一个人遭受丧亲之痛时,他可能一时无法面对,以致把自己的情感封闭起来。此时,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就像心理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处于“暂停状态”。然而,当时机合适时,他就会意识到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他必须深入挖掘所有被埋藏的情感,并与朋友、读者或听众分享自己的经历。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走向更广阔、更深刻的人生。
作家戴维·洛奇曾指出,我们所认为的写作实际上有90%是阅读。因为你不仅是在写作,还要经常回顾已写的内容,这样你才能够知道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和改进。对他人故事的挖掘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回顾过往的经历。这样做的目的是努力培养思维的灵活性,使我们能够从多个角度看待同一个事件,找到看待所发生事件的其他方式,并将悲剧置于更宏大的故事背景中。正如玛雅·安吉洛所言:“你越了解自己的过去,你就越自由。”
本文摘自《如何了解一个人:看见与被看见的艺术》,[美]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著,肖志清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0月。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发布于:上海
https://k.sina.cn/article_5044281310_12ca99fde02002g7a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