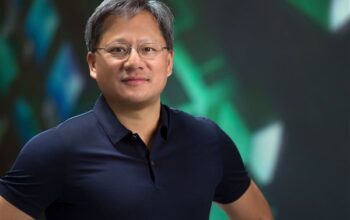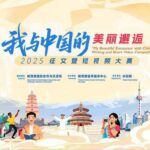转自:长安街知事
如果说上一轮技术革命还让人有时间慢慢适应,那么人工智能(AI)这波浪潮,直接把社会带入“加速度时代”。
AI会对就业带来哪些影响?创造性岗位就一定安全吗?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有价值的工作”?国考打破年龄限制又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劳动经济学会会长蔡昉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采访时说,AI不是简单的“抢饭碗”或“换饭碗”,而是一把同时创造与破坏的“双刃剑”。它带来的生产力红利巨大,社会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共享AI红利的制度。在这场没有旁观者的变革中,问题不再是“AI要不要来”,而是我们如何让技术真正服务人、造福人。
要建立一套共享AI生产力红利的制度
知事:当下社会对人工智能与就业的关系存在“抢饭碗”和“换饭碗”,您认为哪种更贴合实际?
蔡昉:我认为两者都有。AI被认为是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甚至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技术革命,它和以往所有颠覆性技术变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创造新的岗位,也会淘汰旧的岗位,这两种效应会同时、强烈地出现。
劳动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从工业革命到今天,技术变革总是“先破坏,再创造”。比如,许多今天存在的职业,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不存在。每一轮技术进步都会催生新的职业类别。
但问题在于,岗位的创造与消失之间存在时间差。失去工作的这一代人,未必等得到新岗位的出现。研究表明,人们改变职业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要经过一代人。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别担心,新的岗位会来”。对于那些被技术淘汰的人,必须通过就业支持、社会保障和生活改善等手段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劳动市场。
更关键的是,社会要建立一套能够共享AI生产力红利的制度。毕竟,AI带来的利润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不仅属于企业,也属于整个社会。企业理应获得创新带来的收益,但社会同样应通过再分配机制,共享这部分红利。

11月15日,广东深圳,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图源:视觉中国
重新定义“有价值的工作”
知事:您在书中写道,AI可能替代的不仅是低技能劳动,也包括创造性岗位。那我们该怎样重新定义“有价值的工作”?未来哪些类型的工作会成为中国的“新蓝海”?
蔡昉:过去的技术替代主要集中在重复性、危险性或体力劳动上,人们因此形成了“教育水平越高越不容易被替代”的判断。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一样。它具备强大的认知能力,能在几秒钟内吸收、处理大量信息,这意味着它不仅会替代部分白领岗位,还可能影响到创造性、知识型工作。
未来,AI还会赋能机器人,而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全球最多的机器人装备。这意味着蓝领岗位也会再次面临替代。因此,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哪类岗位最安全,几乎所有岗位都有被替代的可能。
但这未必是坏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人类从资源约束中解放出来,能够提供更多满足需求的产品与服务。那时,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职业”,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或一般性的服务,而应包括一切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他人或自身精神需求的活动。
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随着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这种“按需而劳”的设想或许会部分实现。社会应通过再分配和公共产品供给,让每个愿意工作的人能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即便他的劳动没有直接的市场需求。

11月8日,浙江乌镇,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迎来首日观众。图源:视觉中国
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学习
知事:您怎么看“十五五”时期的就业形势?在人口变化和AI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动高质量就业?
蔡昉:当前就业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灵活就业比例高,但灵活性容易带来不正规性;另一方面,部分劳动力从城市回流中小城市或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一老一小”两类人群的就业困难得不到解决,也会降低整体就业质量。
AI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但也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新动力。关键在于如何驾驭AI,让它与劳动者形成互补关系。AI不仅能提高生产率,还能通过“赋能”方式帮助劳动者,让原本不具备入门水平的人达到岗位要求,缓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失衡。
要实现这一点,AI的开发者、企业投资者和用户都应与就业优先战略对齐。比如,企业在使用AI时,不应只追求替代劳动,而要利用AI提高劳动者能力。
同时,要通过教育与培训培养人机协作的新能力。AI在认知领域有优势,但在人际沟通、团队合作、同理心等非认知能力方面,人类依然不可替代。未来照护老人、教育儿童等领域都需要具备这些特有的人力资本。
因此,教育和培训要面向AI时代的人机互补需求,强化劳动者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更加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受技术冲击和就业困难人群提供兜底支持。
人工智能既是挑战,也是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劳动力结构的契机。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能否让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人的福祉。
国考打破年龄上限,释放双重导向
知事:今年国考公告明确,报考者的年龄限制由过去的“35周岁以下”放宽至“38周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上限也由“40周岁以下”调整为“43周岁以下”。您怎么看国考打破“35岁上限”,透露出何种信号?
蔡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符合时代趋势的信号,它至少释放出两个重要导向。
第一,它体现了反对年龄歧视的理念。我们一直在强调劳动力市场要包容不同年龄群体,但以往法律和政策层面缺乏具体落实。这次放宽限制,可以看作是一个现实起点,也为未来在立法上进一步反映这种理念打下基础。同时,这也与延迟退休的改革方向一致。
第二,它顺应了寿命延长与职业周期延长的现实。过去人们50岁退休、30岁就不再考虑再学习;但如果退休延到60岁、70岁,那么40岁、50岁继续深造完全合理。这一政策为更多“大龄学习者”和“再就业者”打开了通道。

3月15日,武汉,湖北省公务员考试,图为湖北大学考点。图源:视觉中国
此外,它还契合人工智能时代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逻辑转变。过去我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但现在,一次性教育已不足以应对AI带来的快速技能更替。未来,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回炉”,不断培训、再教育、更新知识。
这不一定非要靠读硕士或博士实现。可能是一门两个月的微课程,一个技能证书,就能重新进入职场。教育、培训、工作将形成循环往复的过程。
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5-11-21/doc-infycuaa1345762.shtml